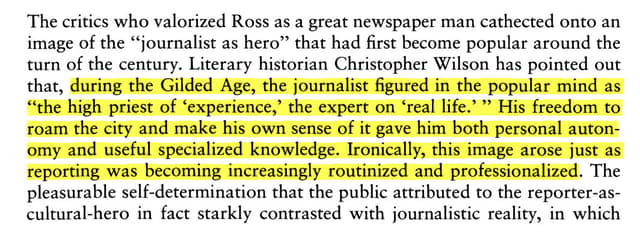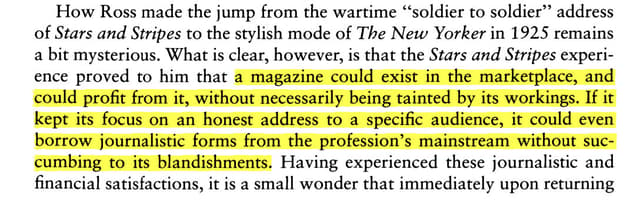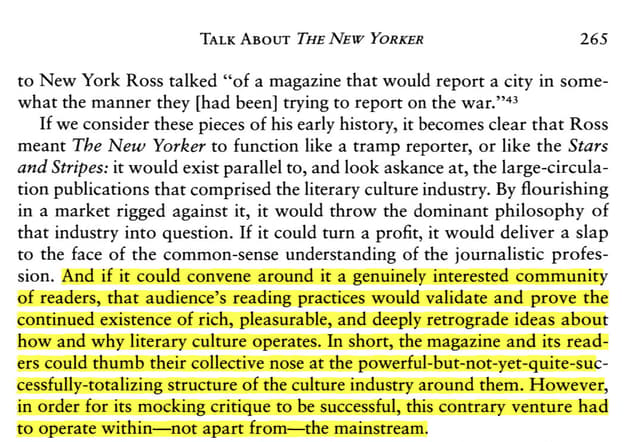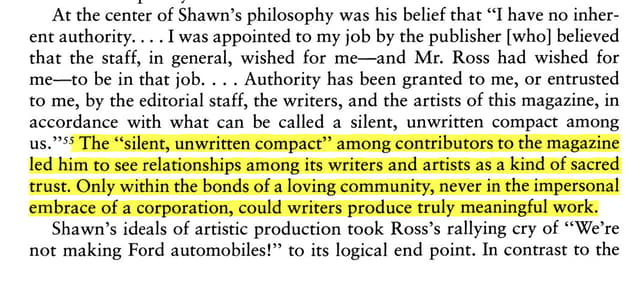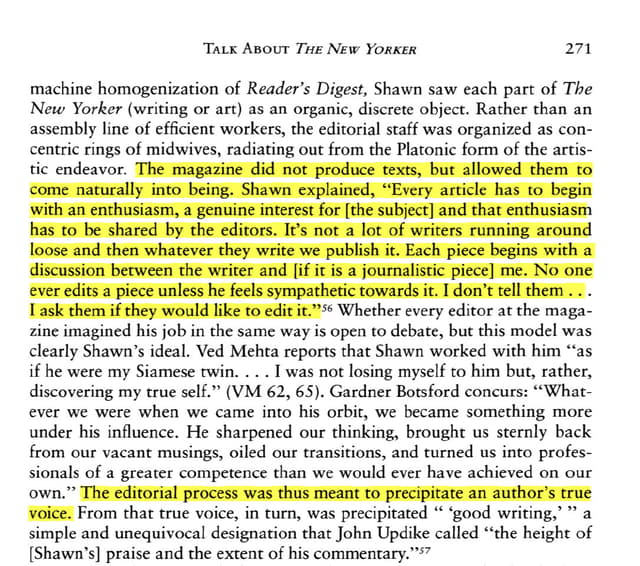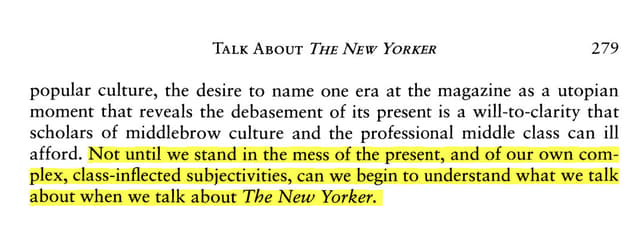在镀金时代,记者在大众心目中被视为掌握「经验」的大祭司,「现实生活」的专家。他自由地漫游在城市中,自主地感知城市,这同时赋予了他个体自主性和有用的专业知识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记者这种形象的建立,正值报道越发变成一种循规蹈矩和职务行为之时。
一本杂志可以在市场上存活并盈利,而未必受其运营活动的玷污。如果一本杂志始终诚实地与特定受众对话,它就既能从媒体行业的主流中借用新闻的形式,而又不会屈服于主流的油滑。
如果杂志能够围绕自身召集一个真正有兴趣的读者社区,那么 […] 它和读者就有能力对周围强大、但尚未完全统治的文化产业结构嗤之以鼻。然而,这种嘲讽批评要想成功,就必须在主流之内逆流而上,而不是远离主流运作。
供稿人之间「沉默的、不成文的契约」让他将杂志的作者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神圣的信任。只有在一个充满热爱的社区纽带内,而不是在一个无人性组织的裹挟中,作家才能创作出真正有意义的作品。
杂志不产生文字,而是让文字自然而然地产生。每篇文章都必须发端于热情和对主题的真正兴趣,并且编辑必须同时具有这种热情。编辑只会编能让他产生共情的文章。[…] 编辑过程的目的是沉淀下作者的真实声音。
只有让自己置身于当下的混乱中,置身于自我那种复杂的、受阶级影响的主观性中,我们才能开始理解,谈论《纽约客》时,我们在谈论什么。
What We Talk About; When We Talk About: The New Yorker https://t.cn/A6Sa8nsd
Please be advised that this post was written or last updated a while ago and may therefore contain outdated information or opinions I no longer hold.
请知悉本文自写作或上次更新已届相当时限,或包含过时信息及观点。